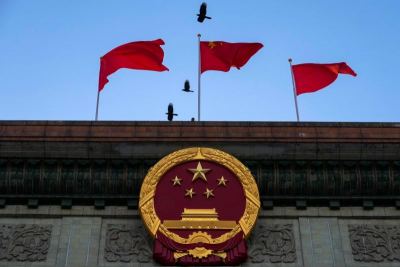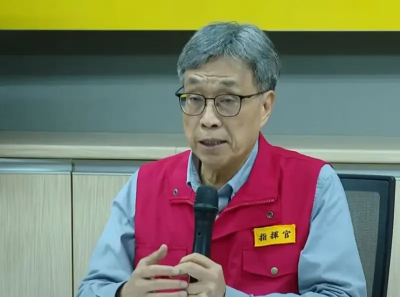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被影迷簡稱「PTA」的保羅.湯瑪斯.安德森,《黑金企業》、《霓裳魅影》等片更多次等片更多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,生涯作品更累計入圍28項奧斯卡獎。他曾以《心靈角落》獲柏林影展金熊獎,《戀愛雞尾酒》、《黑金企業》與《世紀教主》更讓他創下影史唯一橫掃坎城、柏林與威尼斯三大影展最佳導演的紀錄保持者。《一戰再戰》並未於任何國際影展首映,自九月底上映至今,全美票房累計一億七千萬億美元,持續穩居北美票房前十。
改編自托馬斯品欽的小說《葡萄園》,故事描述美國加州,「法國75隊」反叛軍巴柏佛格森(李奧納多迪卡皮歐 飾),他與革命世家千金「Perfidia Beverly Hills」相愛,在女兒剛出生的時候,經歷了一場情節曲折的反叛軍「大圍捕」;時隔多年後,當時倖存者佛格森帶著女兒薇拉(Willa Hills)躲避鄉間,然而佛格森與這群地下革命者,仍舊逃不過極右派白人至上主義的陰謀論祕密組織「聖誕節探險者俱樂部」成員洛克爵上校(西恩潘 飾)使用政府警方與軍方優勢武力的暴力圍剿。
一群前革命者時隔十六年重新聚首,當年「大圍捕」時,招供叛徒的陰影仍在,如今昔日殘存戰友一個接著一個落網,當年叛徒「Perfidia」的女兒薇拉卻成為洛克爵首要追捕的目標。故事千回百轉,佛格森必須克服自己的地下組織認同失憶(永遠想不起的「行動暗語」),找到音訊全無、正在被地下組織成員援救,卻安全仍舊堪慮的女兒。於此同時,父親內心的祕密,女兒的身世之謎,正在發酵。
《一戰再戰》故事的迷人與精彩,於我而言出現在電影一開場就出現的幾個細節,溫吞的炸藥高手佛格森,即便與身為黑人、女性「Perfidia」相愛,他問她該做些什麼,她告訴他,我要「亮眼」大秀。電影片頭便有如此台詞:「我要你創造一場大秀,這是一場革命的宣言,好好弄,弄的精彩、弄的亮眼。」(I want you to create a show. … This is the announcement of a revolution, Make it good, make it bright.)其實光從人物的名字就已經暗藏玄機故事的核心,「Perfidia」在拉丁文中就代表「背信忘義」,即便「Perfidia」與佛格森相愛,卻陰錯陽差地與洛克爵上校玩起危險、充滿性張力的精神角力。電影開場,在Perfidia遇上洛克爵上校時一觸即發。電影台詞是這樣寫的「起來!」(Get up!)、「不是你的腳要站起來,既然我們要玩這場遊戲,我要你下面給我站起來!」(Get up. No your fucking feet.Since we are fucking playing! Get it up! )
我們不得不注意到,這種「硬起來」、「大秀」的美學,在「PTA」的劇本中,巧妙將品瓊原著的女性都改為黑人讓人直接聯想到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(BLM)組織(三位創始人均為黑人女性)的行動,以及該運動衍生出至今仍活躍的多樣化、遊擊戰型態的民間自發組織。更甚者,許多「黑人民權運動」參與者的後代,仍舊活躍在美國社會運動的最前線,就像故事中的「Perfidia」便是出身「革命世家」。革命人士也是有世家和貴族的,同樣的菁英主義慾望,就像那些反猶的美國洋基白人試圖組織的陰謀論神祕組織「聖誕節探險者俱樂部」。
所以,這個革命故事,有種族、有性別、有階級、有歷史、有菁英團體,更重要的是,這些交織再一起,在美國的脈絡下,這一切很「性感」。這層充滿慾望的感性,讓這個找出「背叛者」女兒身世之謎的家庭故事,這個整部片最後才開啟的「麥高芬」,多了一層神祕的電影幻象。一切似乎來自一場無意識、深藏潛意識的出軌慾望,極左與極右的交媾,這象徵著一種極左陣營內在的精神疏離、失序混亂、路線碰撞。一種務實、安全、避世的自由派左的實踐性格,和一種精彩、亮眼、硬起來的背叛者靈魂。
但對我來說,這種失序狀態是一種「二重家庭結構」的失序狀態。首先,是美西左派社群中,作為「人」,各自家庭內情慾與夫妻關係的處理,當多元包容的反種族主義與女性主義賦權的推進,這個社群內部隱藏的一種潛在的背叛與疏離的危險。這點顯現在Perfidia的母親告訴佛格森的話:「你不適合我女兒。」其次,是另一個層次上,「左」,無論是哪一種左派,「建制派」(這部片沒有出現)、「無政府主義者」、「非暴力社會運動行動者」,將「同志」同路人作為一個廣義「家庭」之後,其內部的精神認同失序、與失憶的狀態。
PTA這場「把希望寄與下一代」的戰鬥故事,表面上拍的光鮮亮麗,幾乎像是一部動作電影,槍戰、追車、肉搏樣樣都有,拜品欽小說之賜,政府與反抗軍雙方,都有著複雜的組織結構,試圖揭示了一種從七O年代延續至千禧年後,甚至綿延至如今「川普時代」的一種時代映照。
雙重結構的第二個層次發生在十六年後,一場背叛之後,曾經謹慎保守的佛格森,如今頹喪毒蟲,彼時此刻都懦弱羞怯,差別在吸毒到腦袋壞掉,「連反抗軍的暗語都想不起來」的他,要怎麼找到會合點,找回自己人生最珍貴的女兒、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?他一直試圖透過電話,與總部以密語聯繫,手機沒電還要找充電器、插座,就是回答不出總部的謎語:「時鐘上沒有指針,現在幾點鐘?」謎底是這樣的:「時間並不存在,但它還是宰制著我們。」十六年過去,總部的服務人員告訴佛格森這是人盡皆知的革命者守則,他認真翻出就能找到,但曾經保守務實的他,如今荒誕昏迷,大夢初醒的他哪有時間翻書?宛若不存在的不只是時間,而是曾經(被背叛)的記憶。但它宰制我們。
PTA宛若是把一場左派內鬥、背叛、繼承大戲,拍成了一齣好萊塢民主黨選舉宣傳影片,若本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(個人認為機率頗高),那就是最完美的「homecoming」。李奧納多迪卡皮歐飾演的那位,無用的、沒有血緣的父親,仍舊是你的父親,就是美國民主價值最美的展現。巨蟹座的PTA當然要把一個左派被壓迫的戰鬥故事,拍成一個家庭故事,彷彿佛格森找回女兒,一則家庭故事的「回家」,對PTA來說,就是好萊塢民主黨找回失序川普時代精神認同的終點,而下一代接棒的未來自然光明無窮。
對我而言,「PTA」一直都有移植美國「新好萊塢」(New Hollywood)時期,電影巨匠勞勃阿特曼(Robert Altman)最擅長的「眾生喧嘩」(cacophony)多線敘事野心。「PTA」試圖將這種美學,從阿特曼的七O年代政治陰謀故事,移植到「2000s」年代以降的企圖心。從《心靈角落》、《性本惡》,到《一戰再戰》,他部部劇情流暢、剪接緊湊、選樂完美、表演到位、攝影機調度驚人,他似乎成功過一次又一次,卻沒有真正觸及美國的陰謀論魅力。勞勃阿特曼傑作《納許維爾》(Nashville,1975)中,千回百轉的多線交織,最後會聚一堂的「眾生相」,這幅圖像服務了一場在現實政治中曾經、正在繼續發生的陰謀。而陰謀,是「非意圖的結果」,阿特曼用一種看似更宏觀、更高層次的視角去組織不同人物、觀點、場景,這卻是一種當是被創建的寫實主義模範,卻在每一場「眾生喧嘩」中,無論攝影機距離遠近,卻貼近融入環境中的小人物自身,當下的一個個情感片刻。
在勞勃阿特曼手上,這些片刻卻無比真實,許多大場面透過多角色同步收音,事後在剪接台上對每一個小人物,選擇哪一個片刻,甚至透過蒙太奇組織其他場景製造「一個小人物的小事件」,與「這個大場面他的小舉動」,最後堆疊出這些都是「這個世界精神演進」的一環。
反觀,《一戰再戰》的電影主體在「十六年後」,約佔者部片五分之四,佛格森的精神認同失常,李奧納多的特寫鏡頭無疑是全片焦點,配角人物的表現雖然優異,但本片處理主人翁「家內情感失衡」的主題異常清晰。
因此筆者認為,品欽這層後現代主義的荒謬,對後七O年代至今凝滯的世界狀態的批判,在「PTA」鏡頭下似乎有些被「劃錯重點」。當然對「PTA」電影美學而言,暴力與背叛回歸「家庭溫暖」合理的選擇,成為一場又一場精場的場面掉度,最後成為好萊塢社群的精神價值依歸,本片或許終於能成為「PTA」成功封王,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。況且,除了開場稍微有些深入的「Perfidia」的出軌戲,幾乎都是「側面」描繪暴力。這已經是導演剪輯版,沒有片場閹割的問題。
一場場精彩追車、圍捕、兇殺場片固然技藝精湛,電影可以只拍一條情感線,但當你已經有了雙重結構,沒有好好扣題就有些可惜。自然也無法回應小說金句背後的弦外之音,例如,為什麼左派集團的背叛者總是喜歡更大更美的場面?左派的精神疏離(性冷感)是否導致以性作為武器的行動者特別容易成為背叛者?
《一戰再戰》電影以父親尋女、女兒政治覺醒,以親情和解,為這個多線交織的故事收尾,其實最後卻僅僅只是回應、處理了前述第一層「家內」的情感疏離的遺緒,卻沒有真正回應正個「大寫」的左派社群失憶、失序紛亂狀態。《一戰再戰》這種無能且無法回應「政治上的家庭」的狀態,或許或多或少呼應了電影外,美國現實世界中的民主黨支持者的精神狀態,寧願在社群、媒介中沈溺家庭幻影,在嶄新分眾化時代的社群連結中製造昇華幻象,卻無法面對真實生活中需要處理的失憶與繼承遺緒。
所以我特別關心,回歸家庭溫暖的佛格森,最後到底有沒有學會使用手機自拍閃光,佛格森最終就是逐漸凋零的老男人,連女兒教他用iPhone「自拍開閃光燈」都學不會。佛格森終究沒有自己想起「現在幾點鐘?」的答案。自拍或許這不是革命必備的技能,但我想知道曾經失憶的他的腦袋,除了還能想起基本的革命守則,是否還能學會新的技術與戰略。面對下一次的政治與情感背叛,面對下一輪十五年,他「除了投票」,還能想起些什麼、做些什麼。
電影最後,父女相認,必須先確認暗語:「我們不再他媽的這麼重要。」(We no longer be that god damn relevant.)
有些事情,遠比找到女兒的解脫感更複雜一些。
●作者:沈怡昕/影評人
●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,不代表《NOWnews今日新聞》立場
●《今日廣場》歡迎來稿或參與討論,請附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,文章歡迎寄至:opinion@nownews.com
- 李奧納多狄卡皮歐
- 名家論壇
- 沈怡昕
- 一戰再戰
- 社會運動
- 女性主義
標題:名家論壇》沈怡昕/《一戰再戰》:無政府主義家庭幻影
地址:https://www.twetclubs.com/post/121496.html